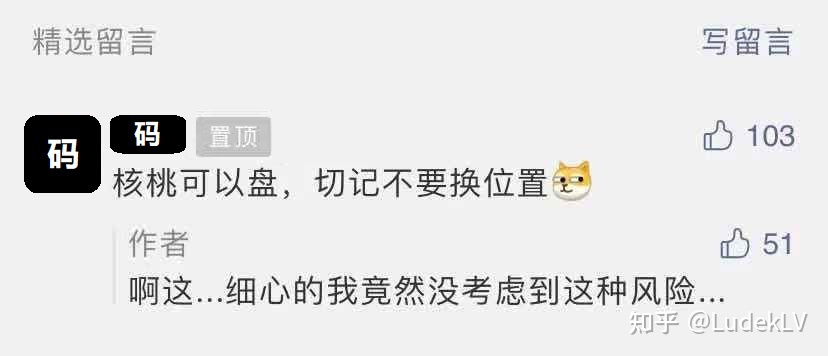|
每当东北大地被奇寒包裹好的时候,每当东北山林伴着漫天大雪发出风啸的时候,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特殊年代中的特殊场景,它们不是油画,也不是电影中的某个或多组镜头,而是,经过大脑的精神发酵,瞬间形成的不可磨灭的旷世杰作。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一个年关将近的冬夜,密林的空地上燃着一堆鲜红的篝火。大雪纷扬,山峰摇曳着长蛇般的火苗,那簇明亮发光的火焰,经风一吹,不时发出呼呼的声音,旺火之上,吊着一个不大的陈旧瓦罐,瓦罐里升腾着袅袅热气。一位高大的将军,不时用那双大手往瓦罐里添雪。 在篝火的四周,靠卧着十多个疲惫不堪的孩子,他们都是抗联一军少年营的小战士。夜深了,大雪依然不停地下着,山风依然不停地呼啸着,在零下近四十度的这个冬夜,孩子们疲惫至极,或靠或卧蜷缩成一团,不知是醒着,还是睡着,一动不动地寂静着。 将军怕把孩子们冻坏了,他一边忙活,一边不停地逐个拍打着孩子们,让他们起来活动手脚。有的孩子哼哼两声,或翻了身又深深地酣睡过去。将军很无奈地摇了摇头,笑了笑,随即挺直腰板,从怀里掏出匣枪,大声吼道:“紧急集合!”孩子们于睡梦中突然被这洪亮的声音惊醒,愣怔了一下,旋即提起枪,咧咧歪歪地站在了将军的面前。将军看了看孩子们,又发出一道跑步走的命令。将军打头跑在最前面,孩子们背起枪跟在后面,围着篝火跑了起来,不知跑了多少圈,将军觉得身上热乎乎的,才命令孩子们停下,让大家围坐在那熊熊燃烧的篝火前。将军往火里又加些木头,把煮沸的雪水分发给每个孩子。瓦罐不大,一圈下来,水就所剩无几了,将军起身,又去捧雪,那些银光闪烁的雪,被丢在瓦罐之后,瞬间融化,水就慢慢浮上来,稍顷,孩子们便又听到瓦罐里传出的“咕咕嘟嘟”的声音。 “还冷吗?孩子们。”将军亲切地问了一句。孩子们齐声喊道:“不冷了,杨爸爸!” 望着孩子们稚气未脱的脸庞,将军瘦削而又有些倦怠的脸浮现出了慈祥的笑容。将军又加了一些柴,篝火再次噼噼啪啪地燃烧。在这个呵气成霜的冬夜,这堆散发着微不足道热量的火,却给将军和孩子们带来了无限温暖,无限希望。 将军靠在一棵高大的树干上,他让孩子们围拢在他的身边,靠在他的胸上,趴在他的腿上,然后,将军把羊皮大衣抻开,盖在孩子们的身上,看着这些少年营的孩子们渐渐睡去,他才合上早已困倦的眼睛。 翌日,晨光微露,雪住了,篝火已熄,将军的眉毛、胡子挂了一层浓重的白霜,羊皮大衣上也落满了一层雪,而孩子们的身上却片雪皆无,一觉醒来,身上还冒着一些热气。 将军带领孩子们埋上残火灰烬,传令他率领的部队开拔转移。 少年营是将军一手建立起来的,最大的十八岁,最小的也只有十一二岁,他们有的是烈士的遗孤,有的甚至是在路边捡来的,还有的是自动加入为父母报仇的。这些孩子在将军的身边迅速成长起来,和其他战士一样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。孩子是将军的心头肉、手心里的宝贝疙瘩。 将军除了军事公务外,许多时间是和这些孩子们待在一起的,尤其是在冬天。行军、打仗、宿营,他就像父亲一样呵护着这些孩子,为他们洗脚、挑泡、暖脚,真可谓关怀备至,孩子们都亲切地呼唤将军为“爸爸”。 这个温暖的冬夜,只是这个严冬的花絮。这年冬天奇冷,冷得枪都拉不开栓。在敌人日夜围剿的日子里,部队每转移到新的地方,再也不敢点火了,白天还好些,当夜幕笼罩山林的时候,可苦了孩子们了。冷风刺骨,夜宿难眠。频繁的转移,频繁的行军打仗,根本不可能搭些窝棚,今天转移了,明天不知又在何处。于是,将军就带领这些孩子们垒雪墙,雪是孩子们的童趣,垒雪墙的过程中,将军也变成孩子了。 雪墙垒得又厚又高,捡些柴草铺在地上,将军就搂着这些孩子们窝在里面,从讲故事开始,慢慢地进入梦乡…… 这个冬天的故事,是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部队野营拉练时,听东部山区老乡讲的,讲这些故事的人,有汉族,也有朝鲜族,后来成就了《呼啸军魂》长篇抗战小说中的一些情节与场景,也成就了即将完成的另一部长篇抗战小说《冷冬》。 在那个年代的冬天,将军与孩子的平凡故事里,我终于参悟到他们在绝难时,所展现出的革命友谊与人性的光辉,燃烧着火一般的情与义! 当下,每年的冬天,吉林的东部山区便成了旅游胜地。人们聚集在那里或滑雪,或赏景,或泡温泉,煮雪饮茶,或品尝山林特产,或点燃一堆篝火,一边喝酒一边歌舞。镜头里珍藏起无数美好幸福的画面。即便是大雪纷扬、山风呼啸的三九天,人们依然享受着饱有诗意的游历与生活。 我们赶上了好时代!和平年代的繁华盛世,衣食无忧,愈加期待未来的无限美好。 那年那月的冬天,山林里的那堆篝火和篝火旁的将军与孩子;那些为后来人抗击日寇、光复失地、收拾旧山河而宁愿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……今天的好日子是前辈们用生命换来的,我们不该忘却,至少,以冬天的名义,凝固冬天的记忆! 那个冬季比春天更暖。 |